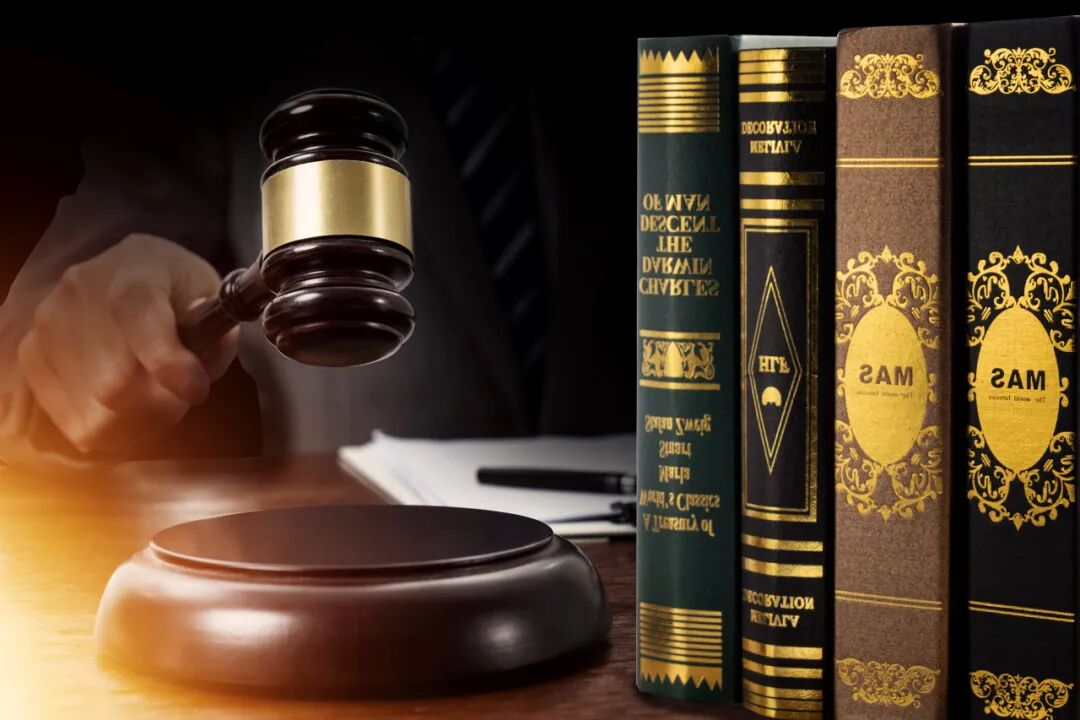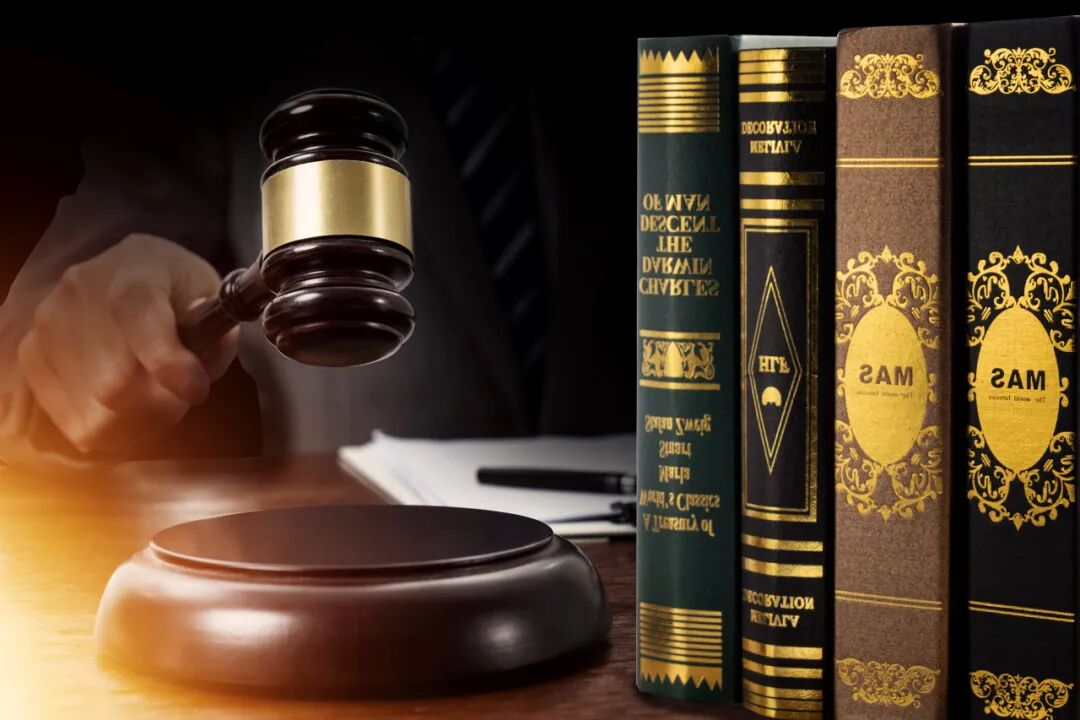在上篇中,我们已梳理了中国大陆与中国台湾地区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立法背景、发展历程与法律构成要件:两岸虽同循“司法先行、立法跟进”的路径,却因社会经济环境与法律实践差异,形成了“实质控制导向”与“形式股东限定”、“类型化细化”与“原则性抽象”的不同规范逻辑。然而,法律制度的生命力终究体现在司法实践中——当“刺破公司面纱”从法条文本走向个案裁判,两岸法院如何认定“滥用行为”?如何把握“损害结果”与“因果关系”的边界?典型案例又折射出哪些制度适用的共性与差异?下篇将从[两岸司法实践与典型案例分析]以及[法人人格否认制度价值、挑战与未来展望]两个部分阐述。 第三部分:司法实践与典型案例分析 一、大陆司法实践与案例 中国大陆地区的人民法院在适用法人人格否认制度时,主要依据为《九民纪要》等提供的类型化标准,其判决说理往往呈现出一种严谨的“三段论”式逻辑结构:即大前提(法律及司法解释规定)、小前提(案件事实)、结论(是否构成人格否认)。 由君伦所代理的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近期审结的一起跨境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系“横向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司法实践。本案中,七家境内外金融机构组成的银团向香港注册的一家控股公司发放近亿美元贷款后,遭遇借款人实际控制人失联、资金转移、工厂关闭的系列违约事件,由此引发对九名被告的连带责任追索。 201*年8月签订的《贷款协议》约定由银团向该控股公司提供三年期贷款,一家境外集团公司及一名自然人提供连带保证。贷款分两笔发放后仅月余,该控股公司实际控制人父子即告失联,资金去向不明。银团随即宣布贷款加速到期,并通过抵销权实现部分债权受偿。此后多年催收无果,最终诉诸司法程序。 针对境内六家企业,法院通过股权穿透分析发现:其中四家公司系该控股公司的直接或间接全资子公司。更关键的是,这些企业存在法定代表人高度重叠、注册地址集中、经营范围趋同等典型混同特征。在银团完成初步举证后,法院将财产独立的证明责任转移至被告方,最终四家关联公司因未能证明财产独立、经营分离,被认定构成人格混同,需承担连带责任。而另外两家公司因证据链断裂得以免责。 法律适用方面,虽合同约定适用中国香港地区法,但基于借款人主要财产所在地、用款地、关联公司注册地均在中国大陆地区,依最密切联系原则适用中国大陆地区法律,体现司法主权与裁判灵活性的统一。 本案判决生动诠释了新《公司法》第23条第二款关于横向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立法精神。司法实践表明,关联公司确实可能成为法人人格否认的法定责任主体。判断关联公司之间是否构成人格否认的核心标准,在于这些关联公司在人员、业务、财务等方面是否存在实质性混同,以致构成法人人格的混同。在具体个案审理中,对于债权人主张的关联公司之间财产边界不清、财务混同、利益输送、业务平移等具体情形,法院需要综合考量持续时间、出现频率、财务记载情况等诸多因素,审慎判断这些行为属于关联公司间正常业务往来,还是已经达到足以认定关联公司丧失独立人格、沦为股东逃避债务工具的程度,并据此作出是否否认关联公司法人人格的裁判。 二、中国台湾地区司法实践与案例 虽揭开公司面纱理论(又称法人格否认制度),于2013年始增订于台湾所谓“公司”法条文中,然于2013年台湾司法实务见解已部分肯认此原则之适用,例如于台湾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50号民事判决(RCA工伤案)即表示:“所谓‘公司法’于102(即2013)年1月30日增订所谓‘公司法’第154条第2项规定前,揭穿公司面纱原则等相关理论已属法理,依民法第1条规定,自得适用之。在个案上,如控制股东有诈欺、过度控制、不遵守公司形式、掏空公司、或藉公司型态逃避法令规范、契约义务、侵权责任等滥用公司法人格之不正行为,致损害公司债权人时,为维诚信及衡平救济,例外地否认公司法人格予以救济,与法人格独立及股东有限责任原则不生扞格。”此判决,亦成为中国台湾地区司法实务届首次明确表态肯认修法前亦有揭开公司面纱原则适用之见解。 中国台湾地区的法院适用揭穿公司面纱之原则时,其审酌之因素多包涵审酌该公司之股东人数与股权集中程度;系争债务是否系源于该股东之诈欺行伪;公司资本是否显著不足承担其所营事业可能生成之债务等情形。如中国台湾地区台北地方法院108年诉字第1722号民事判决指出:“法理并非全盘否定公司法人格独立,仅在个案上,如控制股东有诈欺、过度控制、不遵守公司形式、掏空公司、或藉公司型态逃避法令规范、契约义务、侵权责任等滥用公司法人格之不正行为,致损害公司债权人时,为维诚信及衡平救济,例外地否认公司法人格予以救济。” 然而因为法条规范要件严格,故实务上运用法条时,法院须严格检视股东是否真有滥用情形,如中国台湾地区“高等法院”110年度重上字第455号民事判决中指出:“查系争买卖契约之买方当事人为席OO,席OO并非隐名代理敦O公司缔约,业如前述,敦O公司既非系争买卖契约之当事人,即无负担系争买卖契约买方给付义务可言,尚难认敦O公司负责人许OO有何滥用公司法人地位,使敦O公司负担系争买卖契约之买方给付义务,并因清偿显有困难且情节重大,致使股东藉此脱免债务导致债权人权利落空之情形,要与所谓“公司法”第154条第2项之规范目的及构成要件不符。至陈OO主张许OO担任多家建设公司负责人,并多次以不同公司名义推出建案,屡生纠纷等情,不论是否属实,均与敦O公司并非系争买卖契约当事人一事无涉。陈OO主张许OO应依揭穿公司面纱原则、所谓“公司法”第154条第2项、第23条第2项及民法第1条负系争买卖契约买方之清偿责任云云,并不可採。”即因为公司尚未达到“清偿显有困难”之要件,而无法适用法人格否认制度。 中国台湾地区所谓“公司法”第154条第2项将股东责任限于“滥用公司法人地位致公司负担特定债务且清偿显有困难”之情形,此种严格要件设定可能产生规范漏洞,特别是当股东滥用公司地位却未导致公司负担债务时(例如利用公司形式规避法律强制或禁止规定),即难以适用该条文追究股东责任。值得关注的是,台湾司法实务近期已展现突破传统见解之趋势,中国台湾地区的“终审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744号判决即明确指出:“公司法人格与股东虽具独立性,然若股东滥用公司制度,藉由公司独立人格规避法律责任或契约义务,以达成规避法规范强制或禁止规定之脱法目的,或导致社会经济秩序显失公平时,基于诚信原则与衡平理念,得例外否认公司法人格以资救济。”此项见解实质上已肯认揭穿公司面纱原则得独立于公司法第154条第2项规定而适用,将该法理之适用范围扩张至非以“特定债务”为要件之滥用情形,此一发展不仅符合现代公司法制趋势,更对完善大陆地区法人格否认理论体系具有重大意义,殊值深入研析。 总的来看,中国大陆法院的论证路径更接近于“演绎法”,即从一般到特殊,将《九民纪要》等明确的规则(大前提)应用于具体案件事实(小前提),从而得出结论。而台湾法院的论证路径则更接近于“归纳法”,即从特殊到一般,从个案的具体事实中提炼和归纳出其行为是否符合“滥用”这一抽象原则的本质特征。 第四部分:制度价值、挑战与未来展望 法人人格否认制度作为股东有限责任的必要补充,其核心价值在于矫正权利滥用、维护债权人利益与实质公平,保障公司制度健康运行。两岸制度均面临平衡保护债权人利益与维护公司独立人格及股东有限责任基石这一根本挑战。 随着2023年修订的中国大陆新《公司法》的全面实施,关于“横向人格否认”的司法案例将大量涌现,甚至还出现了跨境的“反向人格否定”的案例(如君伦代理的由广东省高院2024年审理的一起合同纠纷案件中,君伦律师主张债务加入与反向人格否定均获支持,在二审阶段为境外银行逆转确认数千万人民币债权),这将是对新法条的实践检验。可以预见,最高人民法院未来可能会通过发布新的指导性案例或司法解释,对横向否认的具体适用标准(例如如何认定“利用控制关系”“逃避债务”等)进行进一步的细化。 而中国台湾地区则需要在保持司法灵活性与增强法律可预测性之间寻求更佳平衡点,想必也非轻松挑战。 中国大陆与中国台湾地区在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构建上,分别走向了“体系化、精细化”与“弹性化、原则化”的两条不同路径,这背后反映了两种不同的立法哲学和对司法角色的不同定位,各有其优劣。两岸同宗同源,法理相通,在未来的发展中完全可以相互借鉴。中国大陆地区在规则细化和体系构建方面的成功经验,可为中国台湾地区在增强法律确定性方面提供参考;而中国台湾地区司法实践中灵活运用法理、追求个案实质正义的智慧,也值得中国大陆地区在面对日益复杂的新型案件时学习和借鉴。通过持续的交流与对话,两岸可以共同完善这一重要的法律制度,为促进一个更加公平、透明、有序的市场经济环境贡献力量。